
近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發布《網絡犯罪案件審判白皮書(2019—2023年度)》,通報該院近5年審結的網絡犯罪案件辦理情況。其中一起“窺私”案例引起廣泛關注。
被告人巫某某通過技術手段獲取某品牌攝像頭的用戶名和密碼數據庫,將其置于自建的App中。其控制的攝像頭超過18萬個,場所涵蓋醫院、家庭、養老院、實驗室等,向“客戶”收取68元至688元不等的會員費,并提供實時監控畫面。最終,法院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巫某某有期徒刑5年,罰金10萬元,并沒收其違法所得80余萬元。
該案例對于公眾隱私安全再次敲響警鐘,在偷拍風氣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的情況下,攝像頭生產、運營的相關企業,必須盡全力提升自己的安全技術水準,為用戶的隱私和安全筑牢防線。與此同時,公安機關等加強對偷窺黑產的全鏈條打擊,也顯得至關重要。
從近幾年各地公安機關的執法情況來看,對偷拍源頭的打擊,已經一再加大力度。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都通報過各種專項行動,并取得一定的震懾效果。但除了從源頭上打擊偷拍犯罪,按照“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的原則,也有必要在終端加大對偷窺者的打擊力度。
像巫某某這樣的人之所以敢于鋌而走險,就是因為這種“冒險”回報巨大。如果沒有那么多偷窺者愿意付費購買監控畫面,那這種違法的生意就不可能如此猖獗。從執法打擊的角度來說,偷窺者因為數量巨大、發現難度更大,在執法環節確實面臨困境。而且,偷窺者散落分布于各地,跨區域執法也會消耗比較大的執法成本。在執法力量有限的情況下,這可能也難以成為常態的執法重點。
另外,按照目前的法律,除非偷窺者用監控畫面對受害者進行威脅、敲詐勒索等,一般都較難被發現。就算發現了,違法成本也不會很高,通常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罰款或者行政拘留,而夠不上刑罰的程度。不容易暴露且違法成本低,這可能就是大量偷窺者能夠躲在暗處為非作歹的原因。
盡管存在這些現實制約因素,考慮到偷拍黑產的危害程度,還是應該在偷窺者環節有所發力。比如巫某某的案件中,哪些人付費購買了監控畫面,應該不難查到。在這些偷窺者中,如果能揪住一些比較惡劣的人員,進行罰款或者行拘,相信也會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偷窺被發現的風險很大,哪怕只是給予行政處罰,很多人可能也會有所忌憚,從而降低購買偷拍畫面的市場規模。
總之,偷窺者也是作惡的一環。相比源頭的打擊,過去在這個環節的治理上,還存在一些不足。補足這方面的功課,相信有助于形成打擊偷拍黑產的合力,對于公眾的隱私安全起到更好的保障作用。
據紅星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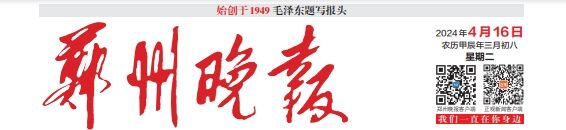

《鄭州晚報》版面截圖